□ 法学洞见
□ 胡水君(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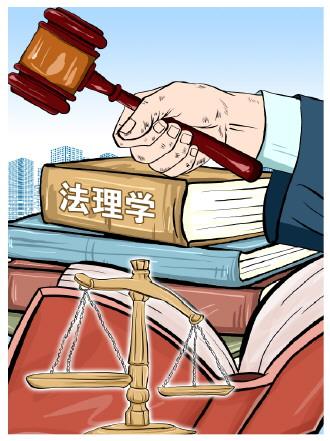
1832年,奥斯丁的《法理学的范围》出版。在法理学的历史长河中,这是一个标识法理学转折的细微点。法理学的古今之变,在这一点上得到充分展现。《法理学的范围》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在法,确定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,并由此划定法理学的范围。自然法在西方传承上千年,因为看不见、摸不着,不能得到实证研究,被奥斯丁划出法理学的范围。也因此,奥斯丁成为西方法学史上实证法学的开山人物。这种实证法学显然迥异于古代自然法学。
法理学的这一历史转变实为近代化进程的一部分。从学理看,本体和自然法是古代法哲学,特别是古希腊自然法学的核心内容。而在现代语境下,由于人的认识立足于经验和理性,形而上的本体和自然法变得虚无缥缈、难以把握、无从谈起,以至于逸出法理学的范围。这是奥斯丁所处的学术境地。奥斯丁未必否定自然法,只不过在他看来,自然法即使存在,也无法进入研究领域,特别是科学和实证研究领域。
奥斯丁基于经验和实证立场划定法理学的范围,足以引出这样的法理学问题:形而上的、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本体和自然法,何以在上千年的时间里长期成为讨论、思考和研究的对象?近现代法理学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,古代法理学则紧紧围绕本体和自然法展开思考和讨论。相比而言,古代法理学显得玄微,近现代法理学比较务实。其间有明显的学术断裂。近现代法理学转而只研究实在法时,在认识论上表现出对本体和自然法的舍弃或隔断。
由于本体和自然法处于形而上的层面,古代法理学通常被称为法律哲学。奥斯丁开创的实证法学,只以可感知、可观测的材料为研究对象,因此通常被归入法律科学。习惯的讲法是,在西方法理学的三大派别中,自然法学属法律哲学,实证法学以及随后产生的社会法学同属法律科学。
其中,自然法学也有古今之变和古今之分。大体而言,古代自然法学的核心在自然法或“自然正当”,近现代自然法学的核心在“自然权利”。近现代自然法学中的自然法,主要是从自然权利引申而来,侧重人的身体、生命、财产和自由,由此看来有更为确实的经验和理性基础。近现代自然法学,尽管相对古代自然法学来看缺少本体和形而上学,但相对法律科学来看又具有价值内涵和理性建构色彩,因而也被归入法律哲学。
此外,诸如康德、黑格尔的法哲学,包含浓厚的思辨内容,是典型的现代法律哲学。这种以思辨为特点的法律哲学,与近现代自然法理论,同属现代法律哲学,与法律科学相区分。无论是现代法律哲学,还是法律科学,都不触及形而上的本体,就此而言,它们又与古代法律哲学不同。总体来说,西方法理学从学理上可区分出三种类型:一是古代法律哲学,二是近现代法律哲学,三是法律科学。
从形而上的本体角度看,古代法律哲学与传统中国的理学在本原上是一致的。古代哲学讲本体,传统理学也讲本体。在中国文化中,本体通常被称为“道体”或“心体”。这是理学的核心。
在古希腊,有一条从巴门尼德和芝诺师徒,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徒,再到斯多葛学派的学术线索。贯穿这条线索的是本体。在哲学史上,巴门尼德被认为是讲本体的早期代表人物。其弟子芝诺通过一系列悖论,表达出本体的静止、无限和永恒。苏格拉底重申“认识你自己”以及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提出“洞穴隐喻”,都幽微地触及本体。再往后,作为自然法思想渊源之所在的斯多葛学派,强调“遵循自然而生活”这一命题,将研究中心聚焦于自然本体和自然法。
在中国古代,同样有一条更长远的从尧、舜、禹,到孔、孟,再到王阳明的学术线索。贯穿这条线索的是道体。同道家一样,儒家既讲本体,也讲法则或道德律。《道德经》中的“天地之间”“天地不仁”涉及本体,“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”涉及法则。本体和法则观念也贯穿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中。《论语》中的“天下归仁”、《孟子》中的“大体”、《大学》中的“在明明德”、《中庸》中的“天命之谓性”在讲本体,诸如《易·系辞》中的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”在讲法则。
从西方学术脉络看,哲学起初是本体之学或关于本体的学问。在哲学中,现象与本体相对应,而现象又为自然法则或客观法则所支配。古代自然法哲学,既触及不可见的本体,也触及虽不可见却具实效的自然法,可谓哲学的原初形态。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和必然性,尤为充分地体现于古希腊诸如《俄狄浦斯王》之类的悲剧所凸显的命运观念。所谓“遵循自然而生活”,既是自觉地顺应自然本体,也是自觉地顺应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自然法则。
从中国传统学术看,本体对应于作用,二者通常被称为“体”和“用”。中国传统学术的精要即在体用论。王阳明曾以体用论串讲儒家经典。在他看来,“正心,复其体也;修身,著其用也”“明明德,体也;亲民,用也”“圣贤教人知行,正是要复那本体”“时习者,求复此心之本体也”。按照体用论,体不变,用则千变万化。就用而言,用可分出旧用和新用,也可分出内用和外用。结合法而言,礼制体系可谓旧用,权利法治体系可谓新用;自然法可谓内用,实在法可谓外用。
合在一起看,现象显示法则,法则支配现象,现象和作用其实处在同一层面。换言之,“用”与“相”处于与“体”相对应的同一层面。置于现代语境审视,本体还对应并区别于人的意志或意识。斯多葛学派的基点,不是人的意识,而是自然本体。相比而言,一如笛卡尔在《谈谈方法》中提出的“我思故我在”命题,现代哲学的基点,在于人的意志、意识或“我思”。在认识论上,从“我思”出发的现代哲学,难以再深入或察知本体。这是包括现代法律哲学在内的现代哲学中的本体衰落景象。
统观古今中西,法理学的三种类型可用法律理学、法律哲学和法律科学来表述。鉴于古代法律哲学和传统中国的理学都以本体为中心,而现代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对于本体都存在认识论上的隔断,古代法律哲学可以中国文化中的“理学”概念表述为法律理学。这是从本体的角度对法理学所作的区分。
在名称上,法律理学既可作为法理学中与法律哲学、法律科学并立的分支,也可作为法理学的总称。按照中国文化的体用论,体用密不可分,有体即有用,有用即有体。从体用不二的角度看,法律理学或古代法律哲学侧重在“体”,现代法律哲学和法律科学侧重在“用”,如此,法理学其实可统称为法律理学。这是既包含“体”,也包含“用”的总的法理学。
从体用兼备的法律理学视角看,法理学有三个基本内容或研究对象:一是道体,二是自然法,三是实在法。由此三重结构,可见只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的奥斯丁的法理学,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法理学,而只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。现代法律哲学并未触及道体,其对自然法的阐述主要以自然权利为根基。总体上,现代法律哲学和法律科学成就的不是礼教或宗教体系,也不是为宗教或道德理论所笼罩的法律体系,而是现代社会的权利和法治体系。
将中国文化融入法理或法理学,需要补充法理学的道体和自然法内容。在“道体—自然法—实在法”三重结构中,道体是“体”,自然法是“内用”,实在法是“外用”,由此所形成的是内外俱足、体用兼备的法理学。
历史地看,中国发展进程中绵延着文脉,虽时有中断,却从未灭绝。沿着文脉审视中国的现代化,这个时代的法理学有着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化需要和历史契机。在全球化格局中,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而言,法治无疑显得重要和关键。形成完备客观的法治体系,为法理的古今中外融合创造条件,为德性和理性的自由生发疏通渠道,现代中国可望接续文脉开创新的文明。
编辑:申旭阳